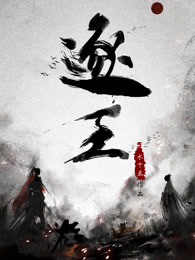零点看书>风流俏佳人 > 第677章 军情如火(第3页)
第677章 军情如火(第3页)
潘简若本是存了三分作态七分真意,只待杨炯软语哄劝,她便顺势纠缠,或撒娇或立誓,总能磨得他点头。岂料他非但不哄,反而条分缕析,句句在理,直指要害,将那军国大义、京城安危摆在面前,堵得她哑口无言。
她满腔的嗔怒与委屈,如同撞上了一堵冰墙,瞬间消散大半,只剩下些许不甘的涟漪。
潘简若心知杨炯所言皆是实情,再要闹下去,非但于事无补,反显得自己不识大体,无理取闹了。
她胸中那口气憋了半晌,终究化作一声长长的轻叹,紧绷的身姿也微微松弛下来,只是那金线繁花的衣袖下,手指仍不自觉绞紧了几分。
潘简若眼波流转,忽地瞥向杨炯那略显疲惫却依旧轮廓分明的侧脸,心念一动,语气也放软了些:“罢了罢了,说不过你这张嘴。只是,你心里只念着倭国那四位姐妹,便忘了谢令君?人家如今也在倭国作战,可也未必不记挂着你这个表弟呢。”
杨炯一听到“谢令君”三字,眉头立时不易察觉地蹙起,方才谈论军国大事的沉稳顿时蒙上一层阴翳,脸上掠过一丝明显的不耐烦,薄唇紧抿,竟是连话也懒得接,只沉默地望着前方喧嚣的长街,仿佛那熙攘的人群比这话题有趣得多。
潘简若将他这细微变化尽收眼底,心下了然。
李潆曾细细与她说过谢令君与杨炯之间的种种纠葛,更点明了婆婆谢南对此事的态度。
她轻轻叹息,声音放得更缓,劝解道:“你也莫要这般不耐烦。有些事,心里不喜归不喜,可面上的功夫总要顾全。你是知道的,娘亲将谢令君视若己出,疼惜得紧。
当初她单枪匹马出走登州,躲过谢家那些明枪暗箭,你以为真是她自己本事通天?还不是娘亲在背后有心送她出去,替她铺路?
娘亲这番苦心,无非是想让她做出些成绩来,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如此这般,娘亲才好在你跟爹面前,在阖府上下面前,堂堂正正地为她说话,给她一个名分体面。”
潘简若见杨炯虽仍沉默,但侧耳倾听的姿态表明他已听进去了,便继续道:“从前你不愿接纳她,娘亲虽心里急,也由着你的性子。可如今不同了,娘亲身怀六甲,正是需要安心静养的时候,你这做儿子的,更该体恤她的心意。
为一个谢令君,闹得母子间生了嫌隙,值当么?况且,日后待你那小兄弟或小妹降生,这府里的光景,谁又能说得准?多一分娘亲的信任与欢心,于你,于我们,于这个家,总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”
这番话,如同细密的春雨,点点敲在杨炯心头。他何尝不明白其中利害?谢令君的存在,始终是横亘在他与母亲之间的一根细刺。
母亲待谢令君的情分是真,那份想成全的心意也是真。杨炯素来孝顺,虽不喜谢令君的某些做派,更厌烦母亲有意撮合,却也从未想过要忤逆母亲,令她伤心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尤其现在母亲有孕在身,更是经不起丝毫气恼。
潘简若的话,剥丝抽茧,将利害关系摆得清清楚楚,更点出了未来可能存在的变数,那个即将出生的弟弟或妹妹,无疑会让本就微妙的家族平衡增添新的变数。
取得父母的信任与倚重,确是他此刻最稳妥的根基。
思及此处,那满心的不耐与抗拒,终究化作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。他并未言语,只是极轻微地点了下头,那动作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,却足以让一直留意着他的潘简若明白他已心中有数。
潘简若见他眉宇间那层阴郁的坚冰终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,心中暗松一口气,知道最难的一关算是过了。
她最怕杨炯牛脾气上来,九头牛都拉不回的倔强。此刻见他虽未开颜,但神情松动,便知自己的话起了作用。
于是乎,潘简若眼珠灵动地一转,心道须得想法子让他彻底开怀才好,免得又沉溺于那些烦心事。可要逗他开心,于她这惯于舞刀弄剑、发号施令的金花卫大将军而言,实在是件比排兵布阵还难的事。
她搜肠刮肚,想着王修平日里那些娇俏可人的小女儿情态,或是耶律拔芹温言软语的体贴,偏生自己一样也学不来。